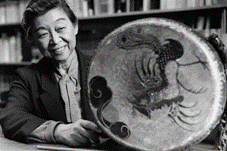2022年4月20日是前哈佛大學榮休教授、民族音樂學家趙如蘭教授的百年誕辰. 哈佛大學音樂圖書館舉辦了「芳音如蘭」 紀念展覧。
卞趙如蘭(1922.4.20—2013.11.30)出身於一個中國學者和音樂家的家庭,父親是趙元任。 她曾在中國和美國兩地求學,先後獲得歐洲音樂史學士、碩士、中國音樂史博士等學位。1947年起在哈佛大學教授中文,1962年開始在音樂系開設中國音樂課程,1974年獲聘東亞、音樂兩系終身教授,成為哈佛大學首位華裔女教授。
展覧展出趙教授的一生精彩瞬間,古籍善本、書籍、樂譜等捐贈,以及她積累的部分田野采風錄音錄像。
展覧將於12月18 日結束。
芳音如蘭Sweet Sounds from Rulan Chao Pian為完全雙語展覧。除文獻記錄外,所有標牌均提供中英文說明。
2013年11月29日, 趙如蘭教授①的女兒Canta(卞昭波)突然發來電子信件,通知我趙老師身體不適。我迫切急於趕去看她,但苦於不能立即離家,丟下身邊四歲的兒子和長期患病的妻子無人照料。正在設法安排從加州趕去波士頓的飛機時,第二天一早卞昭波又來信說,趙老師已經辭世。我的恩師走了。
之前一年,2012年10月,我曾到劍橋,從哈佛廣場步行到趙老師 Brattle Circle的家中向她問安。她形容憔悴,但是一見我來,還是問寒問暖,甚至居然連我的妻子孝惠的日本名字還記得,令我驚訝。我從哈佛廣場的燕京飯店帶來了午餐。那是過去與趙老師、卞先生常去的餐館。我知道趙老師愛吃甜的,特別叫了一份八寶飯當點心,邊吃邊聊。她的短期記憶力已經嚴重衰退,開始重復詢問同樣的問題。不到一小時,我註意到她在發困。但她知道我在身邊,仍強打精神,努力睜開眼,面帶微笑地從桌子另一側望著我,又輕聲問一次同樣的問題。我怕她累,坐了一會兒就起身告辭,從她家步行回到哈佛廣場。沿著一路紅黃交錯的秋色,我徘徊在劍橋斑駁不齊的小磚路上,聽著自己的腳踏著片片幹枯的落葉,回想趙老師憔悴的音容,感到她美麗、慈祥的光芒正在一點一點地離我而去,心中悲情潮湧,悵然若失,很久很久難以平靜。那是我在劍橋走過的最漫長的路。
初見趙如蘭教授
二十三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從得克薩斯州(Texas)高中畢業,到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學院讀本科。我的作曲老師羅伯特·科根(Robert Cogan)從音色角度分析古琴曲《梅花三弄》,給我極大的啟發。受他影響,我分析了衛仲樂先生演奏的琴曲《醉漁唱晚》。科根先生與我討論完我的分析後坦白告訴我,「我已經沒有更多的意見,但是你不妨向哈佛大學民族音樂學家趙如蘭教授請教一下,她很可能會有其他的看法。」於是,經過科根先生的引薦,我給趙老師家第一次打了電話。
電話撥通,從話筒另一端傳來的竟是熟悉的鄉音。趙老師1922年出生在劍橋的Mt. Auburn醫院,但她講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話。我是八十年代在北京長大的。我在北京成長時聽到的多是油腔滑調的京片子,常給人一種誇張、不可靠的感覺。趙老師的北京話非常敦厚、溫馨,絲毫沒有誇張的語氣。似乎隱約能夠聽到只有在侯寶林用老北京話說的相聲中聽到的那種聲音。
記得我們訂下第二天見面的時間後,她說了兩個字,「明兒-見!」她那溫文爾雅的告別令我如醉如癡,仿佛下意識中她的聲音已經開始引導我恍然進入到另一個世界。沒想到,這個電話成了我赴美求學的一個新起點和人生的轉折點。從此我遇到了對我影響最深的一位恩師。
我至今也不知為什麽趙如蘭教授一見面就這樣慷慨地對待我。當我去她在哈佛大學東亞系的辦公室與她見面時,她耐心地聽我這個本科一年級學生匯報自己做的古琴音樂分析,鼓勵之外,提出了她的一些建議。緊接著,她就開始充滿好奇地詢問有關我自己作曲專業的問題。本來電話上約好見面二十分鐘,不知不覺談話已經超過了一個小時。不久後,她就和她先生、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學家卞學鐄教授一起來看我在學校參加演出的音樂會。記得第一場音樂會是我在學校參加合唱團演出奧爾夫的Carmina Burana。趙老師和卞先生聽完音樂會,邀我在學校附近的Pizzeria Uno餐館吃宵夜。
老實講,我對這頓宵夜至今很難忘懷。那時我是一個窮學生,每天只有一美金的夥食費,常常不得已勉強靠一天一頓飯湊活過。因為酷愛讀書,一到波士頓的中國城看到「世界書局」,我就忍不住對中國文化的強烈饑渴,用飯錢買了唐詩宋詞等書,經濟更加拮據。所以,一年中僅有幾頓飯吃得飽。那天晚上的宵夜就是那一年中的少有的一頓飽飯。
遺憾的是我沒有緣分做趙老師正式的學生。我的專業是作曲,而我認識趙老師時,她已經準備從哈佛大學退休。但是後來趙老師成為對我各方面影響最深的老師。她對我的傳授,是從我為她搬書開始的。
第一堂課
趙老師的藏書是出名的。她退休時,要將她在哈佛大學辦公室內的幾千冊書裝箱搬回家。知道她需要幫忙,我覺得自己作為年輕人出出體力是理所應當的。但是,很快我就發覺這不只是件簡單的體力活。趙老師的藏書涵蓋的學術領域非常廣。要整理,首先需將書分門別類地分箱,而很多書在學科劃分上就有相當的學問。一本書是歸文學、還是史學、還是美學、還是版本研究等等,這常常成了搬書過程中討論的有趣話題。我意識到,趙老師無形中在通過搬書啟發我的思考、測驗我的潛力。她在把她一生珍藏的寶庫展現給我,同時她也在默默地觀察我是否能夠領略到這個寶庫的美麗與奧妙。而我是個愛書如命的人。至今我還能感到第一次接觸這麽許多國粹時的亢奮與心靈震撼。
就這樣,每天將書分類、裝箱、搬運,幾個月內將三百多箱珍貴的書籍運回趙老師家。這個過程其實是趙老師給我上的第一堂課。
沒過多久,我父親訪美,準備到波士頓來看我。趙老師得知我父母都是音樂學者,就對我講,「歡迎你父親來訪時,你和他一起住在我家。之後你就留在我家住吧!」這一住就是整整八年。
「地牢」生活
在趙老師、卞先生家住,不僅僅是每天吃飽了肚子,而且在精神上給了我人文教養的滋潤。在我二十一至二十九歲之間思想變化逐漸發展成型的關鍵時期,趙老師用她的自然、率真、樸實與天真,重新塑造了我這個微小生命的主體。可以說,她對我的影響不次於我的親生父母對我的影響。而卞先生則用他「雄辯的沈默」,時時在無言中督促我。
我十七歲上高中時只身離開中國,到美國學習生活時立即產生了尋找自己心中的中國的渴望。這個想象中的精神家園是在趙如蘭、卞學鐄教授家生活學習的八年間找到的;是我躲在她家地下室內那間被我的師兄們戲稱為「地牢」的小房內,不分晝夜寒暑分秒必爭地學習、抄寫中國文化經典而逐漸建構起來的;是在撫觸線裝《四部叢刊》如肌膚般細膩柔軟的宣紙時,在她優雅的笑容與溫厚的話語聲中,在她收藏的世界民族音樂錄音錄影裏,在放滿她烹飪的一道道美食的飯桌上,在與來訪的客人們高談闊論爭論不休中, 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
在這間小小的「地牢」裏,聽得到窗外的雨滴,看得到外面樹枝上的積雪,也隱約可見她家前院內日本紅楓的優雅身影。晝夜、風雨、四時,持續輪轉回環。書架圍繞的一盞小燈下,《嵇中散集》、《文鏡秘府論》、《妙法蓮華經》、《大智度論》、《維摩詰經》、《世說新語》、《揚州畫舫錄》、《老殘遊記》、《陶庵夢憶》、《園冶》、《焚書》····一頁一頁,如畫、如影、如夢、如戲般映入腦海,掀起陣陣美的沖動。我心目中的中國在一磚一木、一水一石中營造,我對中國文化的深情與信念也在逐日增長。
夜深讀書正酣時,趙老師時常端著「薩其馬」甜點和茶水,親自送到「地牢」裏,打斷我的學習,提醒我別忘了休息一下。這個打斷每每變成我們之間在深夜的燈光下的又一次長談。至今,每當我在中國超市看到「薩其馬」,舌尖品嘗的記憶便立即引起思想與情感的回潮,仿佛又回到趙老師家溫馨的氛圍中。
在她家藍印花布的窗簾與臺布間,趙老師打開她的明琴,教授我彈奏《陽關三疊》。一天,我在客廳練琴,趙老師在廚房。她突然對我說,「你彈得不對。」我想我的音是對的,但她指出的是我的指法有誤。古琴音樂中的旋律不僅是音高組成的,同時也是音色編織的。只有能夠辨識如此細微的色彩變化,才能開始領略這個音樂的美妙。
也是在這藍印花布的窗簾與臺布間,趙老師展開乾隆禦筆的原拓,方誌浵先生收藏的唐琴,翁同龢的手書,張大千的山水。在這裏聽陸惠風先生論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聽哲學家劉笑敢教授談道家思想;聽植物學家胡秀英博士分析廣東涼茶的復雜成分;聽畫家靳尚誼先生講解油畫人物。在這裏讀趙老師的外曾祖父楊仁山居士評註的《大乘起信論》激動得我出了一身大汗;讀京劇大師齊如山《全集》,被他的「無聲不歌,無動不舞,無真器物上臺」的美學原則所折服而神往;與哈佛大學的「李杜」——李歐梵教授、杜維明教授,還有漢詩權威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一起欣賞昆曲;聽葉嘉瑩教授講解《花間集》。至今我還能聽見葉教授吟誦林則徐詩句「花從淡處留香遠」時,她那跌宕起伏的聲調和感人至深的情感。
同樣是在這藍印花布的窗簾與臺布間,趙老師給我介紹了後來成為我非常重要的幾位老師,特別是史學家陸惠風先生,和京劇胡琴演奏家倪秋平先生。我也向她介紹了我新結識的哲學家郭羅基教授,以及許多與我來往的青年詩人、美術家朋友們。趙老師的家成了大家的家,在這裏的聚會使我們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陸惠風先生與郭羅基教授後來都進一步成了影響、改變我人生的恩師。
錢賓四先生曾雲,「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有時一兩件非常小、甚至看似瑣碎的事,卻能夠在無意間體現一個人的內涵,也能夠給人最難忘的印象。
花從淡處留香遠
一次,我們去一個不起眼的中餐館吃晚餐。打工的侍者動作很不利索,我們就坐很久才來招呼我們。而比我們來得晚很多的另一桌客人卻先點了菜。過了很長時間,可能將近五十分鐘,比我們來得晚的那桌客人已經在旁邊酒足飯飽,我們這裏才開始上菜。我可能當時已經饑腸轆轆,覺得侍者對待我們沒有禮貌,心中忍不住直冒火。在我逐漸失去耐心的時候,侍者終於端著盤子上菜,帶著一臉的慌張與窘迫,腦門上冒著汗。就在此刻,我聽見趙老師輕聲地安慰她,「不急,不急,慢慢兒來。」她那麽平靜溫和的語氣令這個侍者既感激又慚愧,而坐在旁邊血氣方剛的我頓時意識到自己多麽粗魯、欠缺同情心!趙老師在無意間又給我上了一堂難忘的課。
一天早上,我在地下室聽到樓上傳來一陣陣奇怪的聲音。上樓一看,原來是趙老師整理廢物時發現一個錫罐子落在地上的聲音帶有像小鑼似的尾音,聽起來十分有趣。她竟像孩子一樣,一邊扔罐子一邊嬉笑,仿佛好玩兒得不得了。還有時,我會聽到她自己,或她與四妹趙小中一起唱她父親趙元任先生②為她們譜寫的歌。她的天真自然、快樂與幽默令你感到她如此地珍惜、享受生活的無窮樂趣;同時,她高雅樸素的氣質,又令你感到一種超越俗蒂的沈穩的內在力量。在她心中,一塵不染,沒有任何世俗的陰影。
趙老師以學術為生活。在自己家中每月與陸惠風先生舉辦「劍橋新語」,邀請來往劍橋的學術名流用中文討論各項題目。這裏成了劍橋華人學者社區的中轉樞紐,是求學者的必經之路。平時她愛去聽哈佛校園的各種演講,我也常常與她同往。有時在一段冗長的演講後,只要能夠聽到一位聽眾智慧的挑戰,就覺得前面二個小時的等待沒有白費。我從這些講學活動中學習到了很多。趙老師言談反應極為靈敏幽默,無論是家中還是公眾場合,她往往用一言兩語贏得大家的笑聲。但她是一個很不樂於表現自己的人。連在私下的交談裏,她也從來不顯露自己的學問或成就。無論多大的成就,她只是輕描淡寫。唯有對自己的學生的成功,她的驕傲與自豪溢於言表。
生活中,趙老師在各方面保護我。我大學三年級時,本來有的獎學金贊助突然被撤,我為出不起學費感到走投無路,但是意外收到學校通知說學費已經解決了。我一直很納悶,直到很久以後才了解原來是趙老師、卞先生背後悄悄幫了我。後來又有兩次,趙老師主動想出資支持我,有時甚至是她找借口給我點生活費,但都被我堅決謝絕。再窮,這樣的禮物是絕對不能收下的。在我獲得碩士學位時,銀行賬號已經變為負數,一貧如洗,但由於趙老師給我的知識,使我的生命無限飽滿,內心快樂而充實。1996年間,她讀了我寫的一篇略帶政治性的信,反對我寄出去。「要是被不懂的人抓住一兩句話,看不懂,又跟你鬧個沒完,不知要浪費你多少時候。犯不上!」我想了想,說,「好吧,聽您的,不寄了。····喲,有點餓,上樓『偷』點吃的。」「對!對!盡量多吃!冰箱裏一大些剩菜!」她平時對我總是鼓勵為主,甚至有時對我的錯誤持縱容的態度,以極大的耐心等待我自己醒悟。這次反對可能是她唯一一次堅決阻止我的行為,出自她愛護我、保護我的深心。
在與趙老師、卞先生生活在一起的八年間,我看到他們很多充滿幽默與童真的生活側面。一次,電視上講美國股市又創下新高點。趙老師像個小孩子似的問卞先生,「學鐄,股票漲啦?」卞先生安靜地點了個頭,沒有作聲。過了一會兒,趙老師又癡癡地問,「那我們的股票也漲啦?」卞先生又點了個頭,還是沒有作聲。
他們之間最經典的一次對話是:趙老師問,「學鐄,星期三是禮拜幾?」 卞先生仔細想了一想,回答說,「星期三——是——禮拜四。」然後兩人一起點了點頭。你們看,這兩位大學者之間的對談多麽富有禪機!
2014年3月30日,我幫助在哈佛大學組織了為趙老師、卞先生舉行的紀念會,有上百人從各地趕來參加。趙老師的大弟子榮鴻曾教授在紀念會上操琴演奏了當初趙老師曾教我彈奏的《陽關三疊》。琴音響起,直撥心弦,仿佛立即看到趙老師慈祥的音容回到眼前,令我潸然淚下,不能自已。耳邊隱約又聽到葉嘉瑩教授用跌宕起伏的聲調吟誦,「花從淡處留香遠」。這句詩多麽準確地刻畫出趙如蘭教授一生的為人,以及她為我們每一位學生、友人留下的深愛,令我們無限地思念她!
註釋
①趙如蘭 (1922-2013) 生於美國麻省劍橋市,父親趙元任為著名的語言學家、作曲家,母親楊步偉為早期中國少有的女醫生。十六歲入讀美國哈佛大學女校Radcliffe,取得音樂學士(1944)及碩士學位(1946),之後獲哈佛大學音樂學及東方語文博士(1960)。自一九四七年在哈佛大學任教中國語言,一九六一年執教於音樂系,一九九二年退休,一九九四年被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她的研究範圍以中國傳統音樂為主,旁及臺灣、日本及韓國音樂;著作包括中國戲曲、說唱、音樂史、古琴音樂及書評。對推動中國音樂的發展不遺余力。
②趙元任(Yuen Ren Chao, 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8]),字宜仲,江蘇省常州府陽湖縣(今武進縣)人,生於天津。中國著名語言學家、哲學家、作曲家,被稱為漢語言學之父,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
②梁雷
著名美籍華裔作曲家,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校長傑出教授」。他曾獲得羅馬獎、古根海姆獎、謝爾蓋·庫薩維茨基音樂基金獎、美國國家藝術基金獎、紐約創造基金獎,以及美國藝術文學院頒發的利伯爾松獎。梁雷的薩克斯風與交響樂隊作品《瀟湘》獲2015年普利策作曲獎最終提名。2021年,他的交響樂隊作品《千山萬水》獲得國際作曲最高獎--格文美爾大獎。紐約愛樂、波士頓現代交響樂團、柏林愛樂室內樂團等著名音樂團體曾委約梁雷創作。拿索斯等唱片公司發行梁雷的十張作品專輯。他編著了五本著作,發表中英文文章三十余篇。梁雷曾被聘任為哈佛大學院士協會青年院士,並被世界經濟論壇命名為「全球青年領袖」。2018年,他受周文中先生委托,擔任成立於星海音樂學院的「周文中音樂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及藝術總監。他的全部作品由紐約朔特音樂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