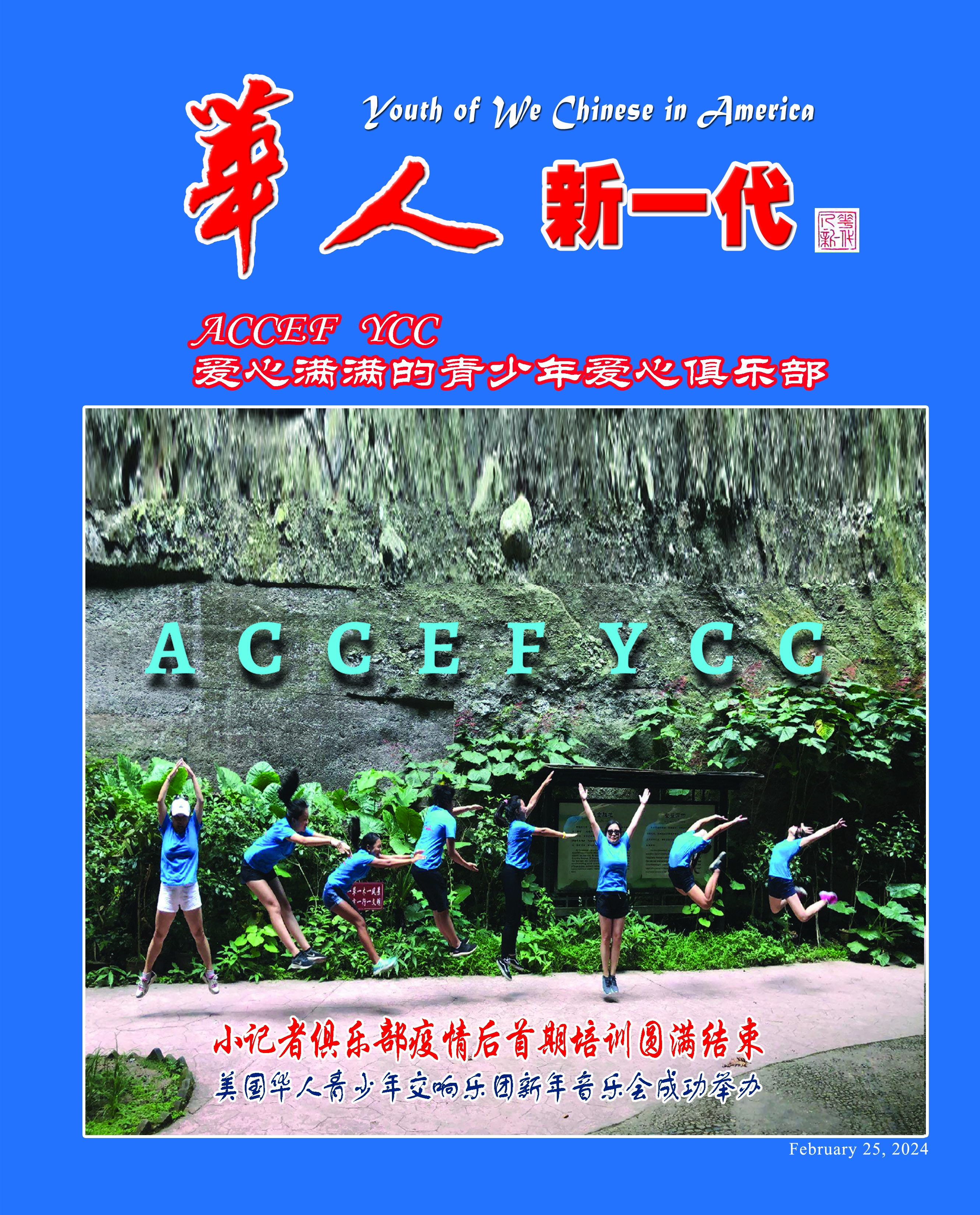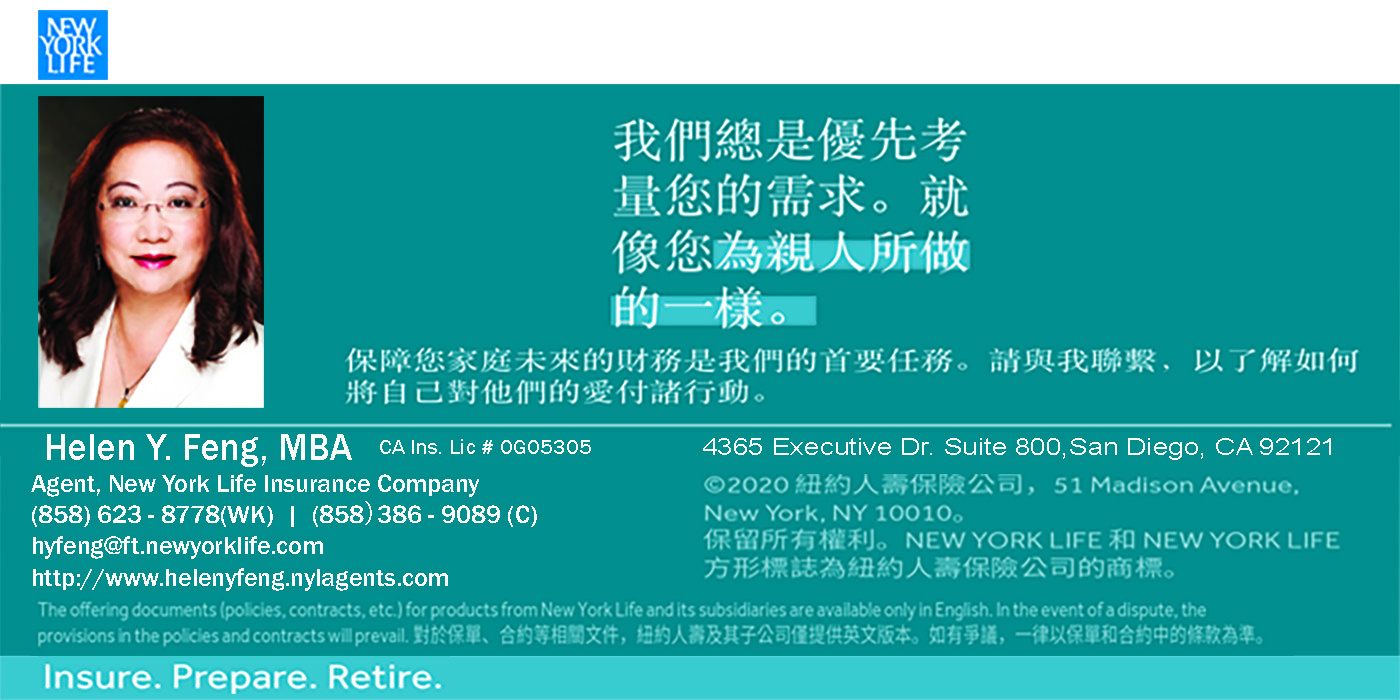美國教授劉凱莉 Carrie Liu Currier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在美國很多大學院校中,通常會先設置用美語傳授的亞洲研究課程(比如亞洲歷史、經濟學、政治學、宗教學、文學……等),而後開出語言課程(如中文、日文、韓文……等),可說語言項目與區域研究之間有一種相互依賴的生存關係。
如果亞洲研究系的教授支持語言教學,就會形成一種雙贏的局面——對亞洲研究有興趣的學生會想學習語言,而對語言學習有興趣的學生也可能會想進一步涉獵亞洲研究領域。
在美國南部的德州克里斯汀大學,就有這樣一位特別支持語言項目的政治學系教授。她研究的是中國政治與比較政治學,憑一己之力在該校創建起一個跨學科亞洲研究項目,同時大力推動該校的外文系開設中文課程。在她的影響下,德州克里斯汀大學在九年前迎來了第一位终身教職制的中文教授。現在,那裡的中文項目辦得有聲有色,設置了從低到高各個層級的語言課程和相關文化課程,並且從無到有開創了中文輔修和主修專業。
而這位政治學教授則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她的家世異常傳奇,本人也一直不斷地利用各種機會學習中文。希望有愈來愈多的研究中國的學者能夠像這位劉教授一樣,不但自己熱衷於學習中文,也能熱情地鼓勵自己的學生把語言學好,從而推動中文項目的建立與發展。
中文名劉凱莉(Carrie Liu Currier),現任美國德州克里斯汀大學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簡稱 TCU)政治系終身教授,博士學位為美國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 政治學系,她自述自己一直是一個中文愛好者。
以下為她的自述節錄:
「有時人們看著我會感到困惑。美國人認為我看起來像亞洲人,而國人則不確定。好幾次去中國的時候,大家常誤以為我來自新疆,有時會問我是不是維吾爾人?我個子比較高,眼睛鼻子看起來不像漢族人,中文發音也有口音,所以不像母語人士。在中國的時候我第一次聽到有人用「混血兒」這個詞來形容我。
我的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中國人。雖然我在美國長大,母語是英語,我小的時候母親也教我中文。然而,我的母語並不是漢語。小時候母親跟我說中文,可是我用英文回答。所以我的聽力比較好,可是我的發音和詞彙常常有問題。
我最終選擇了一個和中文相關的領域——國際政治,現在是TCU政治學系的系主任,之前是該校亞洲研究系的系主任,在 TCU 工作已經二十年了。在 TCU 我教授很多課程,比如國際政治、中國政治、中國外交政策、中國創業精神、全球化等課程。在新冠疫情開始前,我基本上每年暑期都帶 TCU 的學生去中國體驗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我的研究全都和中國相關。
除此之外,我還研究中國婦女的地位,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如何創業,以及中國經濟和中國的對外關係。可以說我對中國的興趣既是個人層面的,也是職業層面的。
我在愛荷華州一個小城鎮長大,愛荷華州的人特別少。我母親在北京出生,在台灣長大,之後來美國認識了我父親,談戀愛,結婚。她來美國的時候沒有那麼多中國人。我出生以後她決定教我中文,那樣她可以有一個小朋友跟她講中文。
我愛學中文,部分原因來自我的家庭背景。我小時候不知道我的家族史很有意思。我的太姥爺(外祖母的父親)叫陶鉅遒,為張作霖工作,幫大帥讀寫消息。我上大學的時候才學到張作霖是北洋軍閥奉系首領,在當時非常有影響力。我的太姥爺也曾經被指派去幫助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我的家族曾經參與並見證了中國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這讓我感到非常自豪。這是我多年以來堅持研究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的太姥姥生了六個孩子,其中一個是我外婆,叫陶鍈,後來她改了名叫陶鎔。我外婆的家人在中國北部,外公的家人在南部,外公和外婆在北京相遇,並在1946年結婚。我外公叫劉敬光, 在廣東省的中山縣出生,是十個孩子中的老大。他加入了空軍成為一名飛行員。中日戰爭的時候,他是飛行大隊的中隊長,執行了多次攻擊日軍在中國陣地的轟炸任務。他曾打下兩架日機,在空軍的歷史書上有他的名字。我和家人都為他是一個中國英雄而感到自豪。
1947年我的母親和她的雙胞胎妹妹出生了,她叫劉玉清,妹妹叫劉玉潔。太姥爺他是在1952年去世的。我的母親和她妹妹也在1950年離開了中國。
因為我的外公參加的是國民黨的軍隊,國共內戰以後他去了台灣。外公定居台灣後不久,1950年媽媽和她妹妹也去了。雖然我的母親是在北京出生的,但她是在台灣長大的。1972年我母親來美國看我阿姨。
那時候,她遇見了我父親。他們相戀,結婚,然後在1974年生了我。我的英文名字叫Carrie Liu Currier,中文名字是劉凱莉。英文名字裡有我母親的姓,因為我外公沒有兒子,所以他想延續劉姓。我沒有兄弟姐妹,小時候也沒有中國朋友,只有母親和我說中文。1979年我的母親帶我去台灣看望我的外公,他不會說英文,所以在台灣時我每天和外公說中文。
回國以後,我的母親找了一所中文學校,我開始正式學中文。在美國,大部分中文學校是周末的社區學校。學校常常設在一個社區中心或者一個教會。那時候我們的老師經常是中國大陸或者台灣來的研究生。那裡的學生很少有中美混血兒,大部分是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ABC的父母都是中國人。在中文學校我們學中文和中國文化。每個星期六我的母親帶我去上中文課。她要我會寫字、看書,不只是會說中文。我的美國朋友都出去玩的時候,我在辛苦地學習中文。那時候很不開心,但現在覺得很值得。
除了去中文學校,我母親也曾送我去過一個中文夏令營。在那裡我學了書法、繪畫和舞蹈。除了學中文,過新年的時候我們還穿中國傳統服飾表演節目。我的表演還上了當地的報紙。
我甚至參加過一個國際文化選美比賽。我赢了,代表的是中國!
我學習中文的經歷跟我的表弟和表姐(我阿姨和舅舅的孩子)不一樣,他們不會說中文,因為沒學。我的母親把我變成了她能夠說中文的朋友。
上大學的時候我也在學中文。在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我主修政治學和語言學。在亞利桑那大學研究所,我的專科是國際政治。這個專業結合了我對政治學和中文的興趣。 2001年我被授予了Fulbright Fellowship獎學金,獲得了一年在北京大學做研究的機會。
我愛學中文,喜愛中國文化,抓住一切可以學中文的機會,包括去中國、看中國電影、和母親打電話、跟朋友聊天。我很幸運,我的家庭從我的太姥爺到外公,再到我母親,都對我有如此積極正面的影響。我愛他們,也因此愛上了中文。」
參考資料:虞莉(2023),美國教授的傳奇家世與中文淵源,取自網址
https://mp.weixin.qq.com/s/syK4-yjxKM71Iw22LZv06w。
《 華人》雜誌總編輯劉麗容與劉凱莉進行深度訪問,以下為摘錄節選:
- 請問妳是怎麼看待自己的?
劉:
我認為身分問題既包括我如何看待自己,也包括別人如何看待我。我認為自己是亞洲人,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是亞洲人。我在一個白人社區長大,那裡沒有人長得像我。我與別人不同,我的家庭也與別人不同。結果大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對待我。我從來沒有很好地融入社會,而且一直是亞裔美國人。在密西根大學,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很多其他亞洲人,我仍然認為自己是亞洲人,但其他亞洲學生並不認為我是亞洲人。那時亞裔美國人還不是很多,所以亞裔學生認為我與眾不同,白人學生也認為我與眾不同。夾在兩種身分之間並不容易,而且雙方都沒有完全接受。如今,作為一個成年人,在我的職業生涯中,人們將我視為亞洲人,因為我慶祝了我的亞洲身份。儘管我住在美國,但我發現中國人很高興看到我說中文並認可我的亞洲血統。我們這一代的許多亞裔美國人他們的漢語程度並沒有跟上,也沒有繼續研究和了解他們的亞洲文化傳統。對我來說,我是誰很重要,對我的職業生涯也很重要。
- 請與我們分享妳是如何在兩種文化之中定位自己的?
劉:
當我年輕的時候,很難知道如何應對我來自不同文化這個現實。這並不容易,跨越兩種文化非常困難。在某些方面,因為我與眾不同,所以我必須接受這種差異,慢慢形成與這種身分相關的自我意識。隨著我對中國歷史、文化、政治和經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很高興地接受了所有以前讓我覺得自己很奇怪,很難堪的「與眾不同」。現在我覺得我的「與眾不同」 很美好。
- 請問是什麼驅使/激勵著妳?
劉:
想過更好的生活——這個動力一直驅著我。我在中西部的一個小鎮長大,但我的家庭有點特別。我的母親是中國人,在中國出生,在台灣長大。我的父親是美國人。我的母親打掃房屋,父親在工廠工作,為了謀生而工作到深夜和週末。我們並不富裕,我總是嫉妒我朋友擁有的東西。我的父母總是讓我努力工作並教導我獨立,能自己照顧自己。這讓我有動力為自己做得更好,我別無選擇。我努力學習,以便能上大學,因為我的父母沒有機會這樣做。我必須獲得獎學金來幫助支付學費,然後必須打暑期工來幫助支付學生貸款。我的父母沒有錢幫助我,當我上大學時,我在經濟上只能靠自己。經濟上沒有人給我安全感,所以我必須努力工作,繼續努力,因為我只能依靠自己。這是我父母灌輸給我的職業道德。他們想幫助我、照顧我,但他們做不到。所以他們教導我要自給自足。
- 請問誰是妳人生中的導師呢?
劉:
我有好幾個導師,他們都幫助過我。高中的時候我的數學老師 Joann Stuhr鼓勵我,曾幫助我建立信心。是她告訴我,女生可以跟男生一樣聰明。是她讓我愛上了學校學習。在大學有兩位研究生 Julie Novkov 和 Joel Bloom,協助我選擇研究所。他們鼓勵我選擇政治學研究所。我父母親沒上過大學,所以我不知道上大學以後怎麼選一個研究所。那時候我很害羞,跟教授說話都很緊張。可是 Julie 和 Joel 幫我,他們教我看研究所需要什麼材料。如果沒有他們的話,我可能上不了研究所。在研究所時,我的教授 V. Spike Peterson 介紹了「女性主義」,為我開啟對此的學術領域大門。她是我的導師及指導教授,和我的好朋友。我上北大的時候她也來中國看過我。最後是我的同事 Jim Riddlesperger 和 Mark Muller,他們兩個幫助我成為大學領導者。
- 請問妳曾經被霸凌過嗎?如果是,請詳述。
劉:
我小的時候,有個小孩子欺負我。他是一個相當受歡迎的孩子,他經常取笑我,也折磨我。他叫我 Connie Chung,一個很有名的新聞主播——在那個時候她是最有名的亞洲女性。現在我會認為這是一種讚美,因為 Connie 很聰明、美麗,是個成功人士。可是那時候我知道那個小孩只是想侮辱我。他有錢,住在我媽媽打掃過的房子的隔壁。他取笑我,也取笑我媽媽和她的工作。 他跟我說話就像我們是他的僕人一樣,他瞧不起我。我小的時候,很多孩子對我都不太好,只因爲我跟他們不一樣。現在我想起来,我還是覺得很傷心。那個孩子不知道他對我造成的傷害有多大,我永遠不會忘記。
- 請問妳對隱性的種族歧視(implicit racism) 及微歧視 (Microaggressionicro)有什麼看法?
劉:
我覺得我們不要做種族主義者。如果一個人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他應該去幫助别人,而不是對其他種族的人存在一種優越感。種族主義來自一種對某個種族的偏見,刻板印象。不管這種偏見,刻板印象好壞,我們都應該根據具體的人或者事情做判斷,而不是基於偏見。我長大的城鎮大部分都是白人。他們常常嘲笑我母親的英文不好,甚至當著面嘲笑亞洲人。 我母親很偉大,她没有理會這些嘲笑,說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她總是昂首挺胸,很驕傲自己亞洲人的身份。
- 請問妳在研究中國女性方面學習到了什麼?
劉:
研究婦女問題對於中國和世界各地都非常重要。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不同的領域──研究女性如何因應經濟改革,以及一胎政策對華人女性的影響。我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經濟對女性的影響上。我的一些研究主要著眼於女性在改革的早期階段從國有企業轉型到私部門時如何在經濟改革中得到幫助。其他研究探討了獨生子女如何影響政策家庭的變化以及各種現代化設施的使用如何幫助女性擺脫更多的育兒責任。比如說孩子的減少和祖父母的幫助(由於孫子女減少)為女性提供了更多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獨生子女政策對改變勞動力和家庭動力發揮了很大作用。關於華人女性,有許多有趣的研究主題,很值得各國的學者學習研究。
8.請問妳認為中國和美國女性的地位有什麼不同嗎?如果是,區別是什麼?
劉: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這些問題沒有可比性,兩國之間的差異太大,無法進行一般性比較。
- 最近一位哈佛大學諾貝爾獎教授宣布了她關於縮小性別差距的研究,請問妳對性別差距有什麼看法?
劉:
性別差異在社會上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社會對男女是不平等的。在某些人的認知裡,女性天生就應該是待在家裡,相夫教子,不需要有自己的工作、事業。 這種偏見讓和男人一樣打拼的女性在工作上處於劣勢。她們很多人比男人更努力、更聰明,但是卻得不到像男人一樣的薪水及工作上的認可或尊重。
- 2023年有四位女性獲得諾貝爾獎項,妳認為這代表著什麼意義?
劉:
每個諾貝爾(Nobel Prize)獲獎的女性都在不同程度上顯示出當今世界婦女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婦女在職業場合上所面對的薪資不平等、性騷擾,和缺乏在一些重要行政職位工作的機會。
2023年有 4 位女性獲得諾貝爾獎,也是女性諾貝爾獎得主創紀錄的一年。
美國勞工經濟學家克勞蒂亞.戈爾登(Claudia Golden)因對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她的重點放在性別差距在勞動市場中及收入方面上的探究。她是史上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單獨獲得此獎項的女性。
納爾吉斯.穆罕默迪(Narges Mohammadi)在人權方面的努力讓她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她是一位著名的伊朗人權運動家,目前正因反對伊朗婦女被受壓迫及促進人權與自由而被監禁中。穆罕默迪女士仍持續抗爭女性在社會中所遭受的「結構式歧視」(systemic discrimination)和壓迫,及促進言論自由努力中。
最後,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o)與德魯.韋斯曼(Drew Weissman)共同開發了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諾貝爾物理學獎則由皮埃爾.阿戈斯蒂尼(Pierre Agostini)、費倫茨.克勞斯(Ferenc Krausz)和安妮.盧利爾(Anne L'Huillier)研發產生出一種脈衝光技術可用來捕抓電子中的亞原子動態影像。諾貝爾獎頒發獎項給卡里科博士和盧利爾博士之所以備受矚目,是因為女性在 跨學科STEM領域佔比不多。獲獎後,卡里科博士談論了她多年來在職業生涯中的許多努力,表明她能走到這一步一路上是多麼的艱辛困難。
每位得獎者展現出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女性,在經濟和職業角色層面上的努力與奮鬥。
- 妳認為現今女性在社會上所面臨最嚴重的議題是什麼?
劉:
我認為有三個對美國和全世界的婦女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是喪失生育自由,第二是針對婦女的暴力問題,例如性騷擾和強暴,第三是經濟不平等。
缺乏生育自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婦女被視為二等公民,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身體。她們無法自己決定是否可以使用避孕工具,能夠選擇胎兒是否足月。在美國,隨著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推翻,這問題尤其嚴重。當女性沒有生育自由時,就表示她們作為一個人,一個女人的自由被剝奪了。生育權是一個全球問題,而不僅僅是美國問題。關於生育自由,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思考這個問題,包括獲得負擔得起的避孕工具、獲得墮胎的途徑,以及抵制強迫墮胎等等。總體來說,我認為女性的身體不應該受到政府的監管。
第二個問題是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例如性騷擾或強暴。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女性被視為男性的財產,並因此受到虐待。女性並沒有像男性一樣受到保護和尊重,得到同等程度的自由和權利,這讓女性不管是在家庭裡還是工作場合都缺乏安全感。
最後的問題是女性和男性在經濟上的不平等。在職場中,女性常常是最後被雇用的人,她們也常常是第一個被解僱的人。她們是受剝削,在工作場所受到的保護很少, 做同等工作,薪資也比較低。這些讓婦女在社會地位、家庭地位上更處於不利地位。
綜合以上,當今世界女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中仍然缺乏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和保護。
- 請問妳對於混血亞裔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呢?
劉:
我覺得非常需要讓亞裔孩子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一個人,有很多和他們一樣的孩子。也許現在他們還不能很好地認知及處理自己的兩種身分。但等他們長大以後,就可以很好地融合自己的兩種身份。當兩種身分合而為一時,他們會為自己的族裔感到驕傲自豪的。 到那時,也許這些孩子就會和我一樣熱愛自己的出生,喜歡自己的亞裔身份,為自己所屬的族裔保持熱情及貢獻一己之力。
- 請問如果可以邀請 10 個人與妳共進晚餐,妳會邀請誰?為什麼?還有會問他們什麼問題呢?
劉:
我會邀請以下十個人:Madeline Albright、Melinda French Gates、Ruth Bader Ginsberg、Kenneth Lieberthal、Angela Merkel、Martina Navratilova、金雪飛(Jin Xuefei,筆名:哈金)、我的外公劉敬光、我母親的外公陶鉅遒和安東尼.塔皮斯 (Antoni Tapies).
我的晚餐嘉賓名單代表了我不同的興趣以及那些已經逝世但有一天我們仍然可能有機會見到的人。他們包括學者、畫家、運動員、作家、慈善家、政治家和我的親戚。
Madeline Albright、Angela Merkel 和 Ruth Bader Ginsberg 都是傑出的女性領導者,在各自不同的領域裡為其他女性鋪平了道路。對於 Madeline Albright 和 Ruth Bader Ginsberg 我想了解她們在職業生涯早期面對逆境的一些方式以及他們個人如何處理這些情況。Ruth Bader Ginsberg 尤其是美國婦女權利和性別平等的先驅。Madeline Albright 和Angela Merkel 我想問她們關於當代政治的問題,她們對當今各種衝突的看法以及他們將如何處理這些衝突——無論是從美國的角度還是從非美國的角度。兩位女性都擔任過重要的全球政治角色,這使她們處於獨特的地位。
Kenneth Lieberthal 是一位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我在密西根大學上過他的課,他讓我對政治學產生興趣。我會問他有關中國的問題以及他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期間所獲得的知識。
Martina Navratalova 是我一直以來最喜歡的網球運動員之一,現在是我最喜歡的評論員。我從小就打網球,看著她以及她整個職業生涯中圍繞著她的爭議。我一直看網球、打網球,喜歡聽她解釋網球策略。我會問她有關網球策略的問題,特別是如何提升我的網球技巧。
對我的外公劉敬光和我母親的外公陶鉅遒,我想問他們關於他們成長的中國。我想知道他們是如何經歷中國歷史的這些決定性時期的。我會問陶鉅遒關於張作霖的事以及與他合作的感受。對於我的外公劉敬光,我會問他內戰期間的生活以及與日本人作戰的感覺。
Melinda French Gates 的基金會為幫助婦女、兒童和發展中國家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情。我讀了她的書Moment of Lift,並受到她的故事和她回饋他人的方式的啟發。我想問她如何確定要開展哪些專案以及她計劃在未來哪些領域投入精力。
Antoni Tapies 是一位西班牙畫家,我喜歡他的作品。他在西班牙 Franco 政權末期創作了許多受政治影響的藝術,而我是他那個時期的抽象畫的粉絲。我想問他的那些 60 年代和 70 年代藝術作品背後的靈感。
最後,金雪飛,筆名哈金,是我最喜歡的作家。我讀過他所有的關於中國歷史和中國移民的小說。我會問他如何選擇故事。另外,我還想知道哪本小說是他最喜歡的或對他來說最有意義的。
- 請問妳認為十年後的妳會在哪裡?
劉:
十年後我仍然想做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仍然在教授國際政治和中國政治,並進行有關中國和亞裔美國人的研究。我希望有一天有更多的機會去中國旅行並帶學生回到中國。 除此之外,我對我的職業生涯和目前的處境非常滿意。
- 請問妳最喜歡哪一本書?為什麼?
劉:
我最喜歡的書是吳承恩寫的《西遊記》(Journey to the West)。這本書我讀了好幾次。每次都能發現一些有趣的新内容,這本書真的很經典。今年我又讀了一次,這讓我想起為什麼我喜歡這本書。每年春天我會在德州克里斯汀大學(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辦幾場和亞洲研究有關係的研討會。参加者都是德州的高中老師。今年我們學習了這本書,他們都很喜歡。那些有趣的冒險故事傳遞了相當豐富的中國文化和歷史,真的很有東方魅力。
- 請介紹妳現在正在閱讀的一本書呢?
劉:
每個星期我都會讀一兩本書。我很喜愛閱讀,遛狗的时時候、睡前的時候都會閱讀,開車的時候就聽電子書。現在我正在閱讀一本叫《榮譽》(Honor)的書,是由Thrity Umrigar 著作的。
17.請問如果有一天的時間可以自由安排,妳會做什麼?
劉:
每天我早上五點起床去打網球,每次和我的一些朋友們打約兩個小時左右。然後我回家遛狗、喝咖啡、看報紙,接著上班。 下班以後,煮晚飯,休息一個小時後接着工作。準備我第二天的上課内容。每天都是這樣子度過的。週末的時候我會多打一點球,有時候,一天打兩次,我是真的很熱愛打網球這項運動。
(劉麗容)